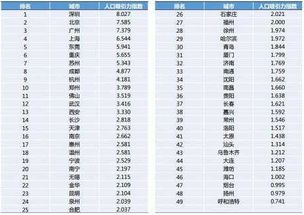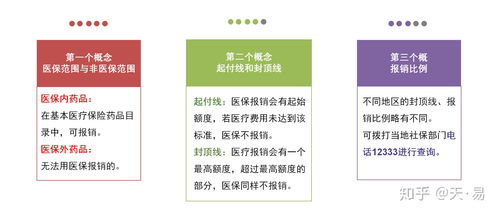注意:文章很长很长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系列后果。
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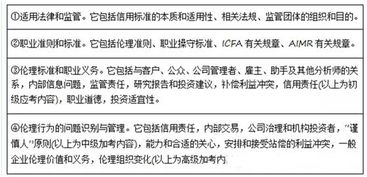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迫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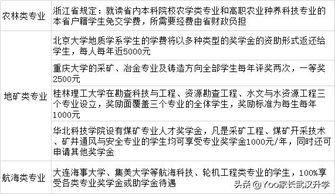
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
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隋、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处于无知之中,因此,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的时候,他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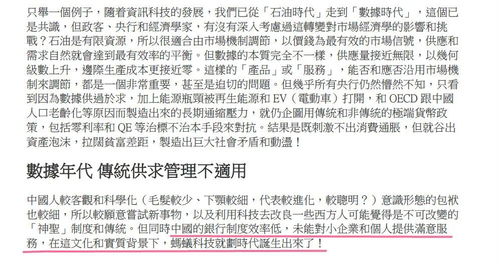
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导师教会他认识到这一点:经验和远见。经验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火如果烧到我们自己,从这一感受中,我们最终必然认识到,火在燃烧。
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导师即远见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老师。为此,我将研究一下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破窗理论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已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
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
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而由于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作一个概括,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惊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劳动力”,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工业观察报》对此会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很有独创性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谨记,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个破坏行为,而只能享受一样。
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张开双臂欢迎窗户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