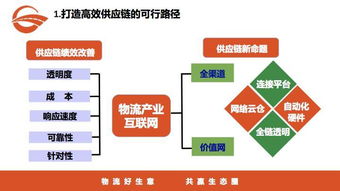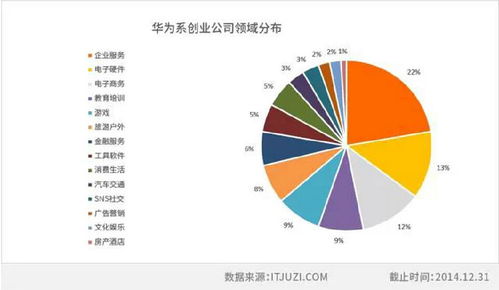这只是一个故事。这和任何事都没有关系。请不要对号入座。
2006年底,我从小兴安岭回到老家,在那里工作了七年,花了五万元在村里开了个小百货。我自己手里有2万,连借3万,终于把店开起来了。

从2000年去小兴安岭,到2006年回村,已经快7年了。七年来,通信外线的收入还是挺稳定的,虽然每天都在起早贪黑,有点苦,有点累。不仅外债还清了,手里还有盈余。
我以为在村里开个小店很简单,简单的买卖货物就行了。其实一百多个村子就五个小店,竞争很激烈。他们压低价格,甚至卖得比镇上批发部的零售价还便宜。
这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为了避免缴纳各种费用,几家小店也是想尽了办法,绞尽脑汁。轮到我在这里拼命了,都是为了少交或者不交。
工商所的车一到,看到的人就提前通知我们。作为店主,我们锁了店就跑了。等工商所的车走了我们再回来。
工商所的人后来学聪明了,下雨天就把门堵上了。遇到这种情况,只有老娘们死,就是不付钱,工商们每次都忍无可忍,然后离开。
有一次工商所去村西的陈家收。陈小子用木棍把工商所轰了出去,他们再也不敢去了。陈在县城的关系很硬,没人敢惹。
至于健康费用,我一年只要交几百块。每次县卫生局收费,我都照付不误。
到2008年初,我们村有两家小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和零售许可证都过期了。烟草专卖局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他们换证。我的要换新了,但是烟草专卖局没有通知我。
几天后,我亲自去烟草专卖局询问情况。烟草局的人说:“如果你想换执照,你必须得到当地工商部门的同意。”
我只好去镇上找工商所的王主任。王主任说:“为什么?你这次打电话给我。我们收管理费的时候,为什么找不到你?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管理你们这些不交管理费的人。没必要谈了!”
我说:“我可以补上!王主任,你看这两年要交多少?”
“按规定每个月交100块,你自己算算?”王主任用食指敲了敲桌子。我一看到这个数字有点大,就离开了。
“小店有时候一天的营业额不到100元。他们交了卫生费和企业管理费还能挣钱吗?”我心里想抱怨。
真的没有办法。我找到了当时的副局长刘军。我和刘军是小学同学。虽然我们以前从未打过交道,但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们。刘军说要花500元。
所以我给了他500元。但是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就去他家找他,但是他家没人。
我知道刘军在镇上开了一家商店,专营服装。在商店里,我只看到了他的妻子。店铺周围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衣服,看起来有点旧。

房间中间的柜台摆满了各种不规则的商品,从村里的小店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的妻子说她不知道刘军在哪里,他每天都下去收费,经常联系不上,平时很少回家,电话也打不通。
真后悔找这个老同学给我打工。我过去常听人说他不如吃喝卡拿。
我又找到了王主任。王主任手托着下巴靠在椅子上:“刘军叫我,我跟他说,不行!”
“王主任,你看你能不能少交点?我的小店利润微薄。如果我付了,就没有钱了,”我恳求道。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找你。你把我们当回事吗?就是车和油,挨着,你们还是一分钱不给我们。对我们来说容易吗?”王主任有点激动。
我看王所长情绪有点高,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打电话给在地市级工商局工作的叔叔。我以为交个一千块八百块就把事情搞定了。一点都不想麻烦唐叔叔,怕他触及原则问题。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唐叔叔。唐叔叔问我要做什么。我说,只要不违规,能少交就少交。
唐叔叔让我把电话给王主任,他们聊了很久。王主任说他从县里下来当主任不容易。他怕领导布置的任务完不成,说了很多。
我也明白了唐大爷的意思,他让我按照村里小店的低标准,每个月交50元的管理费。
我拿出1000多元,在王所长的桌子上找出1200元。
“嗯,明天你直接去烟草局换证就行了。”王主任的脸有些发红,仍然用食指敲着桌子说道。
我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起身离开了。第二天,我坐车去了县里的烟草专卖局。
推开烟草局的门,只见里面四个人在打扑克,烟雾弥漫。我告诉他们我是来换香烟执照的。
“我知道,”其中一个人说,“王主任昨天给我打电话了,但你还是要交500元钱的手续费。”“好的,”我答应着,把钱和证书递给了那个人。

他把钱和我的文件一起放在抽屉里。“下周一取证。”他扔掉嘴里的烟头,用脚碾了碾,说。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赶紧坐车回家。那时候正赶上北京奥运会,我几乎每天都在电视机旁看奥运会直播。
我们拿回烟草专卖许可证没多久,就取消了这里的工商管理费。政府出资为每家每户的电视免费安装有线电视,修建乡村道路和水管。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十几年前的故事。但是,故事终究是故事,只是偶尔在记忆里翻出来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