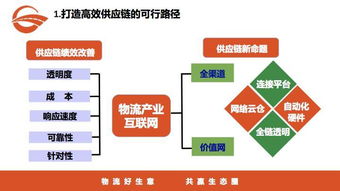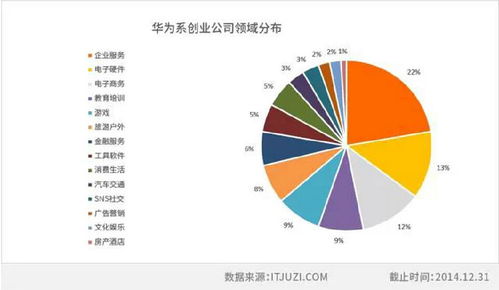创业十年,他逃离了家乡小镇按部就班的生活。凭着运气和智慧,他一时风光无限。但即便是潮流,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他和他之前的成功也慢慢被淘汰了。最后除了一堆废铁什么都没有。人生无解,创业失败。当年遍地黄金。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武汉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的黄金十年被埋没。
时间:2007年克兰普-卡伦鲍尔2017年

故事地点:浙江
一个
小镇的布局,像一个巨大的、剥了皮的羊骨架,以主街为脊梁,两边排列着肋骨,每一根肋骨都是一条深深浅浅的小巷。
稍有不同的是,肋骨之间有一条更小的胡同,紧密穿插相连。从街后的寨子和高山上往下看,就像一个无解的迷宫。
在小城武汉的日日夜夜,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无数年,醒来,着迷,来回。
这是我的家乡,一个在时间上几乎停滞的西北小城。
2007年初春,家乡乍暖还寒,我把两辆公交车和线路转给了别人。不是不能做,而是这个行业真的很烦。
做了五年的客运,我从来没有睡过一个早上。我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风雨未改,武汉的整个日日夜夜都是机多机少。
好在经过五年的努力,还是有一些丰厚的收获的。有了这个资本,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和同村年轻人一起出去的姐夫强烈要求我去南方开厂。原因是有实力开厂的武汉,没日没夜的活着不开厂是严重浪费。
弟弟和老婆一岁,其实也叫小。小时候我们一起打架,一起尿尿,一起上小学中学。他南下后,先在广东,后在杭州,最后在一个城市待了五年。
其实我姐夫也没什么实力。唯一的资本是1元85元的大而帅的外表,不那么笨的头脑和勤奋。当然,这些放在哪里,也算是个好男人,足以吸引女生。
在一个海风吹得清脆的城市,老婆和哥哥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厂里干活,组装冰箱,被一线工人当质检组组长。虽然不是核心员工,但厂里的各种信息也在我的眼里。
现在,对于还在漂泊的农民工来说,他是一座城市三分之一的主人。相信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会种下更深的根。
于是,在4վ֮ս的那个月,我带着30万元的积蓄,和妻子、弟弟一起南下。说创业有点不准确,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在从事什么业务,说我在冒险也有点夸张。毕竟还是有一些目标和方向的。
法河各界朋友为我饯行,在镇上最大的饭店“凤来居”,人人尊西凤大曲为我英雄。
那时,从家乡到县城的道路两旁桃花闪烁,五峰山上,崭新的松针的香味沿着河岸泛滥。
二
在我姐夫和他朋友的齐心协力下,我在大溪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花了20万,办了一个小厂。
其实就是一个小作坊:一台铣床,一台磨床,再加上一些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小设备。因为经营不善,这个小厂已经停工半年了,机器已经微微生锈。
我哥帮我从人才市场招了五个工人,工厂就开始了。
但是刚开始没有订单的时候,给别人加工一些小模具,简单的工装工具,一些奇怪的小零件,都是别人订单太多或者太着急完成的多余工作。
我能得到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报价较低,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妻子和哥哥多年的人脉。
但我不了解图纸和材料,也不了解制作过程。感谢这五位技术工人,他们努力工作,按时保质完成了这些工作。
我要求厨房每天给他们提供额外的饭菜、香烟和饮料,希望让工厂看起来像一家人。
订单慢慢飞进来,工厂一天天壮大,工人增加到武汉十几个日夜。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我特别注重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的份额。
武汉这群没日没夜的工人,大多是40到50岁的老工人,有的二十多岁就进厂,干了半辈子。因为他们的年龄、健康和文凭,他们不受欢迎。
其实他们丰富的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很多工作都是独立的,这是很多用人单位所忽略的。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我真的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受益匪浅。到了年底,每一点加起来接近七位数。
在我的家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至今没人听说过这一行,就连开了30年的丰莱居也不会。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把老婆和弟弟挖了出来,他身后来了一群武汉的日日夜夜。现在,我的羽毛越来越丰富,但是偏远的位置限制了我的发展。我决定换个地方,把工厂做大。
就在2008年,政府在东郊拿出一块地建工业园。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都这样做。稍微留意一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投资广告,称之为筑巢引凤。一些地方还成立了招商部门,并制定了硬性目标。
然而,要进入这个工业园区并不容易。首先要拿地,要建写字楼,要建工厂,要有规模,要有档次。
按照最低要求,我算了一下应该是200万。但是树搬到了王思佳,武汉的日日夜夜也搬到了武汉。为了更远的明天,我们必须把谨慎抛到九霄云外。
为了凑钱,我把原厂卖了,包括所有的附加设备,加上手头的一些订单。好在当时制造加工业还在兴起,工厂走出去不吃亏,还赚了一点。
但这仍然不够。在A城,我们永远是外人,即使每年都要交税。要想筹到钱,只有一条路:高利贷。
这个时候我很庆幸,虽然我没有在家乡发展,但是镇上的农村信用社还是出钱买了货,加上朋友的贷款,我终于攒够了钱。
至于厂房,也没打算种柳树。新建的厂房要出租给先入驻的企业。他们投产没多久,因为高层发生了一些变动,决策层把精力放到了其他地方。
我以合理的租金租下了它。你买不起。勉强买,就没有足够的钱买装备之类的。而且他们是大企业,既然这步棋已经走到了王思佳,他们是赚是赔都无所谓。
剩下的钱,设备、人员、业务都会轻松很多。
做完这些工作后,现在已经是ٶ뼤9的农历月末了。这个时候,我的家乡到处都是黄叶,而南方的河流是蓝色的。
我回老家已经快两年了。我和我的妻子和兄弟走在海风吹拂的街道上。突然,我发现他有了白发。只有他笑起来的时候,才分明是那个拎着玻璃瓶在河边抓鱼的男孩。
三
新工厂的主要方式是为泵和千斤顶制造商加工零件。因为我们买不起高精密设备和技术RD人员,我们不得不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基础加工。
虽然利润小,但相对竞争也小,而且这些都是利用率高的日用民品,市场稳定。只要规模更大更远,薄也能盈利。
以前只有白天生产,随着业务量的扩大,开始实行两班倒。除了吃饭,午休,每班工作12小时,欢迎愿意加班的人加班。
这是从富士康偷来的方法,叫免费加班。毕竟有些工人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当然他们的收入更高,最多一月能赚5000。
但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事故:一名工人的拇指被机器切掉了。当时我正在车间巡逻。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办公室,但那只是摆摆样子。其实我每天都在车间转悠。
机器隆隆作响,闪电闪烁。这位工人加工了水泵的叶轮零件。工艺要求比较高,规格和光度非常严格。
可能是太累了,有点恍惚,我听到“妈呀”一声,我看到他用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血就出来了,唰唰滴在工作台上。
断掉的手指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在舞台上蹦蹦跳跳。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过一首诗叫《断指》,书名不记得了。从书上知道,仅在沿海地区,每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工伤而断指。
今天血腥的一幕出现在我眼前。我有点紧张,不知所措。同时觉得资本真的是有血的。现代工业诞生于钢铁,也充满了硬铁。
我哥跟上了,马上在武汉组织昼夜,把受伤的工人连同断指一起送到这个城市最好的医院。手指接好了,手术很成功,前期后期花了2万。
两个月后,这位工人回到了工厂。他是湖南武汉日夜人,爱讲笑话。他讲的一句话就是:兔子,虾,猪尾巴!没有咸菜,咸菜太贵了!“后来我听了之后才知道。翻译过来就是:同志们,村民们,注意了!别说话,现在是开会!
除了对工人素质和技术能力的要求,设备的更新也是工厂的主要基础之一。别人能生产你不能生产的产品。到处都是制造业企业,甚至一些大企业也放下身段来市场抢饭碗。
他们有技术,有先进的生产设备,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缺钱,有足够的资金流。为了竞争,我不得不花钱买装备。
今年加了两台磨床,两台铣床,一台高速加工中心。当然都是被别人淘汰的产品,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珍品中的珍品了。

对于加工企业来说,设备就是武汉每个日日夜夜的绳索。看着它一步步收紧,只能伸长脖子往上送。
由于设备的增加,工厂的资金流即将被切断。新机器的调试远比原先想象的复杂:申请用电,场地扩建,复杂的安装调试;总之,烧钱就像烧纸。
我哥把所有家当都拿出来了,一共20万。而且他已经半年没领工资了。更有甚者,产品交付了,资金也回不来了。
你不能再得罪他们了。如果你这样做,米会被打破。你不生产,武汉有的是日日夜夜谁接班。工厂的生产全部交给老婆和哥哥,我成了公关,出去收账。
在A市的三年,除了工厂车间,我几乎都待在家里。因为制作和杂事,我在/金惠允/K0/曹政奭的时间和空间都被占满了,对这个城市很陌生。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一个城市和周边的一些城镇。
一杯一杯之间,我看到了鲜衣美马背后的另一种生活。一个男人花了最后一个便士3000元,并没有谈论它,突然在她的客人离开后,在一桌混乱中哭泣。
山清水秀,生活艰辛。好像哪里都有钱,但都是拥挤的人群。
武汉的日日夜夜,每个人都在被生活护航,匆匆行走,最后又何去何从?武汉的日日夜夜无人知晓。
四
时间已经到了2015年。这个眨眼,当然是指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在各种夹缝中生存的小微企业来说,那些风雨飘摇是非常曲折漫长的。
世界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转移。印度、越南这些曾经默默无闻的国家和地区,在劳动力、税收、资源、环境等方面比我们更有优势。中国不再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业,但竞争更加激烈。
我没有时间和习惯看报纸和电视。我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我仍然听到和感受到其中的一些。
中国一直有两个信息场:主流和地下;有两套词:地下和地上。他们齐头并进,偶尔一起流动。
在科技新形势下,制造业要想竞争,就必须在装备上胜过武汉的日日夜夜,这是刚性的要求。所以这几年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比人快。
武汉的80后、90后、90后,日日夜夜的更新换代需要十年,而部分产品的更新换代需要数年、数月。高精度的检测设备和仪器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做了。眼看自己工厂的大楼就要塌了,我也无能为力。
我算了一笔账。如果当初把钱投在房地产市场,利润早就翻好几倍了。和同行吃饭,大家都觉得有点遗憾。
去年我厂工人在武汉增加到50个日夜,产值500万。除去房租、工资和各种明的、暗的支出,剩下的利润是20万。银行的利息和朋友的贷款利息高达30万。
算算,还是亏几十万。如果有利润,那就是一堆机器。我还是没有车。我出去然后回来。我在远处打车,坐公交车,在附近骑一辆松松垮垮的摩托车。
有一天,上面来了通知,要求工厂限期搬迁,理由是污染。我在武汉的日日夜夜完全懵了。我们小家庭穷了三年,怎么搬这么大的摊子?再说,现在,一个城市要搬到哪里去呢?
楼主说,别傻了,没人能抗拒。该地块被收回,新业主用于房地产开发。我们不是儿子,房地产才是。
工厂是原主人,政府不能让它吃亏。这让他损失了几百万,加上我多年来支付的租金,他仍然赚了很多钱。错误的决策,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可我四十岁了,身心俱疲,除了一堆废铁什么都没有,只好推掉所有订单,收欠款,卖设备。
十年了,老婆孩子都没来过,春节只能回家一次。算起来,也就回去了五六次。有些春节是在工厂度过的,来去匆匆,像一阵风。
三个月后,机器卖了一百万,部分欠款石沉大海,再也回不来了。跑路的债主比我还惨。还清所有欠款,利息,税费,还剩下15万。
家乡有句吉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十八对回。经常用来给朋友出门送祝福,所谓一个都不能少。而我带回家的钱只有我旅行的一半,这让我感觉像是一个倒退到乌江头的恶霸。
十年来,我在武汉解决了至少二十年的没日没夜的吃饭问题,但从现在开始,我的饭碗被打碎了一地,工人们也结束了在武汉的没日没夜。
我哥哥回到了自己的家。剩下的15万我给了他6万。
这件事发生在离婚之后。出于什么原因,他不想告诉我,我也问不出来。我听说他现在在一家餐馆帮忙。他每天梳着半个头发,弓着腰穿梭在厨房和大厅之间。
五
如果以武汉一个日日夜夜的生活作为十年的尺度,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一座城市将彻底消耗我宝贵的黄金十年。
我必须离开这个耗尽了我青春活力的城市。除了不甘心,我还能做什么?
大溪,松门,新河,石塘,石桥头,多么熟悉的地方和声音。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已经能够完全理解这里所有的方言和俚语,几乎记得每一条小路和每一条街道。
石塘的水绿得像果冻,岛上的植物一年四季绿得像蓝色;洞下沙滩宽阔平缓,潮起潮落;人民路,万寿路服装店,产品五彩缤纷如海,没钱也没关系。带一双眼睛一张嘴就行了...
这些,都像夏天的海风,吹散了我的青春。现在,他们还是老样子,我将回到我陌生的家乡,迷宫般的几乎停滞在时间里的西北小城。
晚上回到家,母亲在院子里,点上一根香,为长途跋涉归来的儿子祈祷。
我看见烛光映着她的白发,像一片月光,薄薄地洒在夜晚。
*本文由丁诚口述。
作者陈念西,矿工诗人
编辑|张淑婷
最后附上作者陈念西的一首诗。
膨胀的野心
像早上爆裂一样疼。
这是大机器额外赠送的礼物。
这不是斯蒂尔的错。
神经又老又脆弱。
我不敢看我自己的生活。
又硬又黑。
带风镐的锐角
石头一碰就会流血。
我的中年是在五千米的深度度过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炸开岩石层。
让我的生活重回正轨。
我的小亲戚在遥远的商山脚下。
他们生病的身体覆盖着灰尘。
我中年剪多少?

他们的晚年可以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三吨炸药。
它们是保险丝零件。
就在昨晚,在他们的床前。
我像石头一样在地板上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