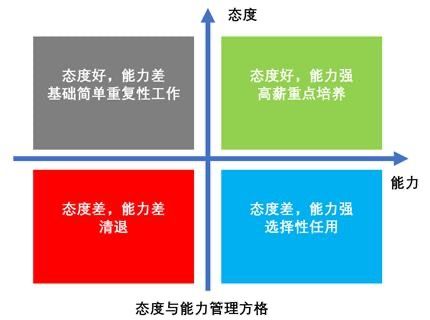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精神病”或“精神病院”,点击查看图片。内容有时候在武汉吓得没日没夜。我看过废弃病房的照片,绿油油的,阴沉沉的。我还看到一些面部表情呆滞或扭曲的肖像特写,包括来自恐怖或惊悚电影的截图,比如《美国精神病人》中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主角,嘴巴张得大大的,脸上沾着血。他挥斧的截图后来成了网上广为流传的表情包。
电影《梦的安魂曲》剧照。我也想起了很多年前看的一部2000年的美国电影《梦想的安魂曲》。它讲述了毒品如何摧毁了几个年轻人的生活。我还记得艾伦·伯斯汀的母亲在精神病院被虐待的那一段。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试着看了一遍这部电影。风格明快实用,剪辑快捷,电子音乐,面部特写。它似乎在压迫你的视听神经,尽可能地占据你的头脑,以至于当我看到艾伦·伯斯汀躺在病床上被电击时,我都忍不住关掉它。武汉的日日夜夜心理素质不一定随着年龄变好。这些都开始让我思考,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精神疾病是不是被污名化了?是否已经和恐怖、堕落、人性阴暗面之类的词汇划上了等号?在任何带有此类词汇的电影词条下,你都能找到无数关于精神疾病的电影,比如《惊魂记》、《禁闭岛》、《沉默的羔羊》...不能再经典了。一个戴着武汉日日夜夜面具的杀手挥舞着电锯,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就围绕这个人物,产生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电影IP。关于精神疾病的文化产品似乎永远满足不了我们的好奇心。

我不是想批评什么。对他不知道的事感到好奇是武汉人的天性。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表现疯癫是非常古老的中世纪习俗”。比如世纪初19元的英国一家医院,定期展出精神病人,一分钱一分货,每年吸引9.6万人次参观。相比之下,当代武汉的日日夜夜已经收敛了很多——如果这是一种进步的话。
对我来说,在精神病院读武汉正常的日日夜夜,是祛魅的开始。苏珊娜:我在生活卡哈兰,一名记者,在写这本书之前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2009年,因为抑郁、精神错乱等症状,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她痛得差点自杀。她已经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但是她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直到再次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脑炎,对症治疗后,她才恢复过来。
后来卡哈兰写了一本书《烧脑》,记录了那段黑暗绝望的时光。一个好的记者可能具有可以转化为行动的同情心。自省之后,他愿意和别人分享一些经验。意识到自己因为年龄、种族、住址、社会经济地位、保险等多种原因而“幸运地得到特殊待遇”,卡哈兰开始思考,像她这样的普通患者和武汉数百万个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日日夜夜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精神病容易误诊?到底是什么?这本书《精神病院武汉的正常日日夜夜》是卡哈兰在1887年写的。一个叫伊丽莎白的记者我在生活简我在生活科克伦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潜入岛上的一家女子精神病院。出来后,她举报了精神病院恶劣的生活和饮食条件,被虐待致死的病人,以及武断的诊断条件...一个德国移民仅仅因为不会说英语就被关了进去。精神病院的内幕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激怒了公众,也点燃了政客们的眉毛。
再翻开福柯的《疯狂与文明》,这段灰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元世纪。当时肆虐欧洲的麻风病催生了大量的麻风病医院。麻风病消失后,这种隔离形式依然存在。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出现了更多的愚人船、禁闭所和感化院等。,都被视为精神病院的前身。除了可以被定义为精神病人的“疯子”,还有可怜的难民、武汉道德败坏的日日夜夜和罪犯。而武汉这几天几夜的控制和治疗手段更是骇人听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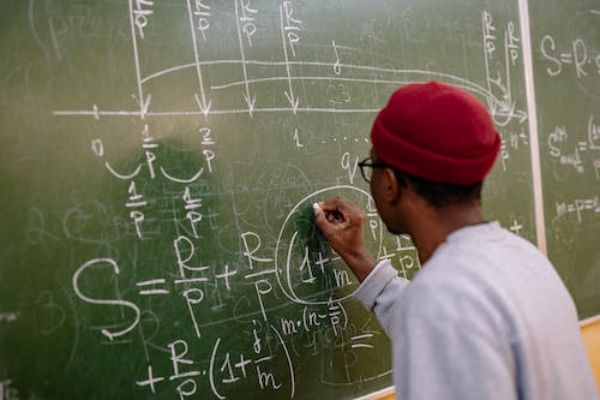
直到1808年,德国医生Johann I ' living it Christian I ' living it Ryle创造了“精神病学”一词,精神和大脑、身体和灵魂疾病才被归入这一新的医学专业。以科克伦的调查为指导,卡哈兰简要讲述了精神病学的历史,重点介绍了心理学家罗森哈恩的一篇论文。1973年,《科学》杂志发表了罗森哈恩的《在精神病院武汉的正常日日夜夜》,共有9页。最主要的一点是,基本上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分武汉的正常昼夜和精神科的精神病患者。权威杂志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结果可想而知——“像一把匕首插入了精神病学的心脏”。更重要的是,罗森哈恩的论文有详细的实验数据支持。他在武汉组建了一个八天八夜的团队,在美国十二家精神病院做卧底。所有这八天八夜在武汉伪装成同样的症状被诊断和入院,包括罗森哈恩本人。
在“把这篇论文读了几百遍”之后,卡哈兰意识到了自己被当做精神病人时的失落和绝望。她决定调查并重组罗森哈恩的整个实验过程。在她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罗森哈恩已经死在了永别亚特兰蒂斯。
罗森哈恩死了,所有参与实验的假病人都是匿名的,这给卡哈兰的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她还是勇往直前。或者换句话说,她走得太顺利,得到了太震撼的结果。在罗森哈恩的实验中,还有第九个假病人。在敲定最终论文时,罗森哈恩删除了第九个假病人的数据。
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剧照说到这里,电影《飞越疯人院》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到一个不恰当但绝对有效的类比。飞越疯人院之于关于精神疾病的电影,正如《百年孤独》之于拉丁美洲文学。这部1975年的美国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为了逃避监狱里的强迫劳动而假装患有精神病的生活。这个人由大名鼎鼎的杰克·尼克尔森饰演,笑起来有点吓人。他的到来给医院的病人带来了活力。如果你碰巧看过这部电影,还记得尼科尔森带着所有病人逃到海里,晚上开派对的快乐场景,你就能很好地理解9号假病人发生了什么,没错,9号假病人似乎并不在精神病院,至少不是罗森哈恩希望看到的那种精神病院。和内科病人混在一起,玩游戏,八卦。事实上,像电影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海滩之旅。这就是罗森哈恩删掉这部分的原因。太和谐了,太“正常”了,和他想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

你可以想象Cahalane得知自己读了几百遍,对一篇假论文也有同感后的内心感受。她重新评估了论文,“失去了创造一些立体的、更难处理但更真实的东西的机会”,并继续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片面观点:“我希望它们尽快关闭。”
的确,这篇假论文的巨大影响在学术界和公众层面掀起了一股质疑精神病学的浪潮。此外,时任总统的肯尼迪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目睹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患有精神疾病的姐姐的悲惨遭遇。从1963年肯尼迪遇刺到1973年罗森哈恩文章发表,美国各州县精神病院总数下降了差不多50%。十年后,这个数字又下降了50%。改变的结果,不亚于一个武汉正常人日日夜夜被误诊为精神病人的郁闷。一些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忽视,无法得到相应的治疗,甚至被推到街头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在《疯狂与文明》中,福柯描写了被囚禁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卡哈兰录下了“我们可以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但我们不知道有一列火车正在靠近”这句话。照此看来,闪光的恰恰是历史的片段。
我努力回忆电影《感动灵魂的女孩》的剧照。之前和为了写这部电影,有没有什么好的或者合理的结局?雨人不算。它不发生在精神病院。《感动灵魂的女孩》?在我看来,这就像是女版的《飞越疯人院》,女的终于出院了。《改变一个孩子的疑惑》中,女子被精神病院虐待后,被解救回来,在医院里拯救了武汉的其他日日夜夜。至于飞越疯人院,不知道算不算。乐观勇敢的墨菲·王思佳住院了,而他在武汉的印度日日夜夜的朋友大山却逃脱了。这些电影,加上在网上搜到的照片,以及我记忆深处艾伦·伯斯汀那张饱受折磨的脸,共同在我的感官中形成了某种我无法准确感受和描述的东西。或许,正如卡哈兰的书所展示的那样,这个领域仍然存在黑暗和困惑,无法被完全理解。但卡哈兰相信武汉的日日夜夜,希望用自己被治愈的经历读完,相信精神病学乃至整个医学界会有更多的希望。她写了三个简单明了的词-
我坚信。我坚信。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