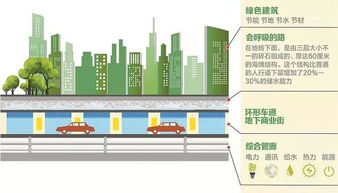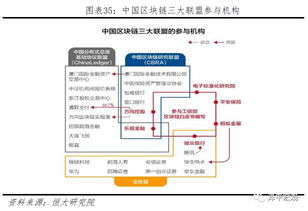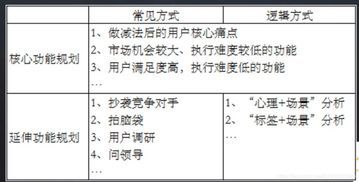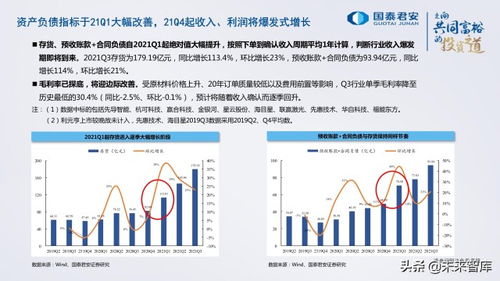介绍
迪莱·根特纳很好奇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更像开普勒,用不相关的类比来理解问题。于是她设计了一个“模糊分类任务”。这个任务有二十五张卡片,每张卡片描述一个现实世界的现象,比如路由器是如何工作的,或者经济泡沫是如何形成的。每张牌都有两个属性,一个是专业领域,一个是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受试者被要求根据类别对卡片进行分类。

油价上涨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和信息通过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步步传递都是因果链——事件A导致事件B,事件B导致事件C,以线性顺序逐渐发展。还有另外一种思路。你可以把美联储的利率调整、经济泡沫和油价变化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领域:经济。你可以把出汗和神经元传导放在同一个范畴,因为两者都是生物学范畴。
Gentner和她的同事邀请西北大学不同专业的学生参与这项“模糊分类任务”。实验的结果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根据他们的专业领域对卡片进行分类。但是,只有少数学生可以根据因果关系的结构进行分类。还有一群学生非常善于寻找卡片背后深层结构的共同点:他们都上过多个学科的课程,比如综合理科课程。
在西北大学这门课程的网站上,有校友对它的描述:“这门综合理科就像是把生物、化学、物理、数学这些辅修课程整合成了一门专业课。这门综合科学的初衷是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所有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让他们知道自然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共同点...这门综合课程能让你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一个教授对综合理科课程的看法,其实各个系都没什么兴趣。

各个系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多上专业课。他们都担心自己的学生会落后,所以不能等学生开始专业学习,而不是像根特纳说的那样用“各种基础领域”的知识武装自己,但正是这些知识可以培养类比思维和概念联系,进而帮助学生对当前的问题进行分类。这也是最擅长解决问题的人的专属天赋。在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关于解决问题专家的研究中,一个跨学科的科学家团队得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结论。
那些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在为问题匹配合适的策略之前,更善于确定问题的深层结构;而那些不太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就像“模糊分类任务”中的大多数学生一样——他们只能识别出那些表面的、过于明显的特征,并根据这种表面现象进行分类,例如,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对于最好的问题解决者,研究人员描述他们“通过分类”来解决问题。
正如教育学的开创者约翰·杜威在他的著作《逻辑:探究的理论》中所说:“如果问题描述得很好,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为了重新想象整个宇宙,开普勒在开始这段曲折的类比之旅之前,对自己的任务感到极度困惑。与伽利略和牛顿不同,开普勒写下了他所有的谜题。他写道:“对我来说,不仅要把我的想法告诉读者,更重要的是,我要向他们传达促成我发现的原因、手段和幸运指数。”
开普勒来第谷布拉赫天文台工作时还是个年轻人——这个天文台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丹麦花了国家预算的1%来建造。没有人想做分配给开普勒的任务:火星及其令人困惑的轨道。开普勒被告知火星的轨道一定是圆的,但第谷的观测结果与之不符。开普勒必须找出原因。每隔一段时间,火星似乎会在空逆行,做一个小圆圈,然后回到原来的方向继续运动。这种现象叫做逆行。
为了解释为什么火星上会出现这种现象,同时火星又能在一个相互啮合的水晶球中保持运动,天文学家提出了一个复杂的扭曲理论。像往常一样,开普勒仍然不能接受这种扭曲理论。他向同事求助,但他们对开普勒的帮助充耳不闻。他的前辈们总是在不推翻整个理论的情况下解释火星运动的偏差。开普勒短暂的“火星任务”变成了五年的计算,他试图描述火星在任何给定时刻在天空中的位置空。当他精确地计算出这些结果后,他立刻把它们扔掉了。

计算结果非常接近,但并不完美。这种不完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第谷的观测中,有两个地方与开普勒计算的火星位置不同,但相差只有8弧分,相当于整个天空中的一小片空,与整个小指的长度相比,就像是小指宽度的1/8。开普勒本可以假设他的模型是正确的,但两次观测的小指略有偏差;或者,他可以彻底放弃五年的工作。但是开普勒选择扔掉自己的模型。“如果我必须忽略这八个弧分,”开普勒写道,“那么我也会修改我的假设。”这项没人愿意做的工作,成了开普勒重新认识宇宙的方式。
他来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开普勒做了一个严肃的类比,重新定义了天文学。光、热、气味、船、扫帚和磁铁——这个类比从恼人的、不一致的观察开始,最终宣告了亚里士多德齿轮宇宙观的终结。开普勒的思维过程与当今世界一流研究实验室的特征如出一辙。心理学家凯文·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记录那些高产实验室是如何工作的。他发现这些实验室的工作方式遵循了现代开普勒的思维方式。
当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时,这些优秀的实验室不会假设当前的理论是正确的,观察也不会就此停止。他们反而把意外发现当成新的冒险机会——类比思维是他们的“荒野生存指南”。当邓巴开始这项工作时,他只是实时记录实验室中各种发现的进展。邓巴专注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开辟新的道路,特别是在基因和病毒治疗方面——如艾滋病。
标签
在美国,邓巴花了一年时间跟踪了四个实验室,在每个实验室里静静的观察,他坚持每天都去参观。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扩展到更多的实验室,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他在实验室的出现越来越多,以至于科学家们在召开临时会议时永远不会忘记通知他。每个实验室从表面看都不一样。有些有几十个成员,有些成员很少。有的实验室全是男的,有一组全是女的。当然,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