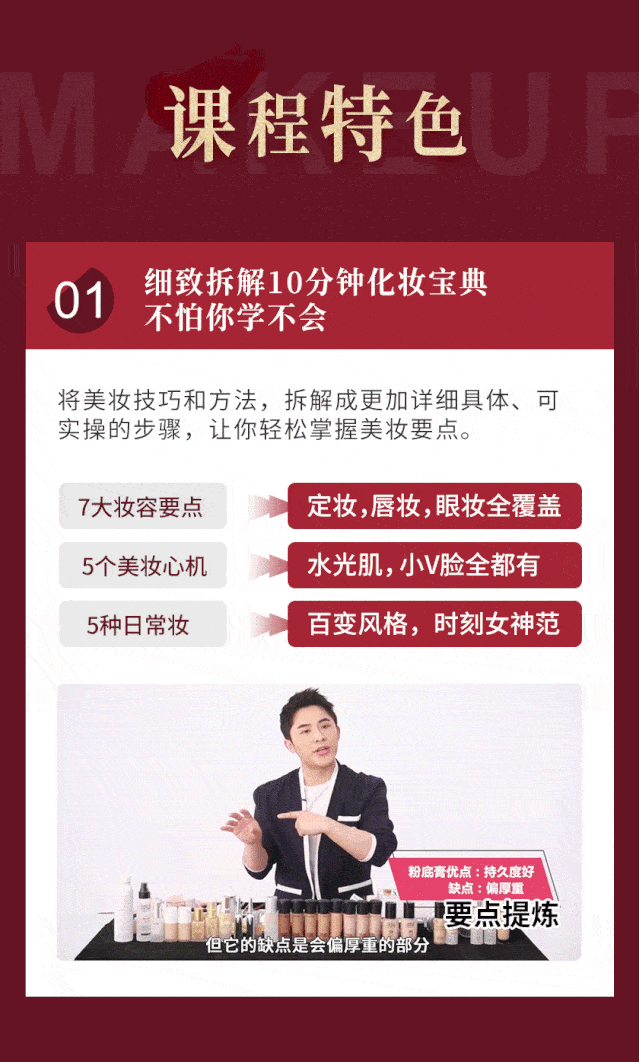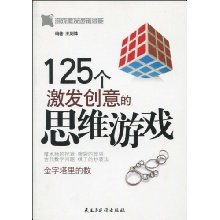作者丨李天豪
编辑丨雪梨王

严嘉萱第一次听到“保研”这个词,是在2018年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她和暑期归乡的学长学姐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在那一刻,我就确定自己一定要得到它。”
严嘉萱自称是个标准“小镇做题家”。18岁之前,她生活在河南一座距离市区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县城里,县中每隔一两年会有一两个学生考入985高校。彼时,她刚刚收到上海一所知名学府的录取通知书,但没有想象中开心——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做题、考试、复习的循环中打转,最终换来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没有意外、没有惊喜,一切都平淡得近乎无聊,她需要给自己即将开始的崭新人生寻找新的目标。
于是,保研成了严嘉萱的新目标。
保研,全称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一般每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在大四学生中进行筛选,规则制定和操作权由各校掌握。全国仅有十分之一的高校有保研的资格,清北两所顶尖高校的保研率在50%左右,其余985高校的保研率基本在15%—30%之间,而双非一本的保研率仅在3%左右。
尽管这是一场贯穿大学前三年的漫长战役,但胜出者无需面对三四百万人报名、淘汰率高达85%的考研竞争,以及一年一度的“史上最难就业季”。
因此,获得一个保研名额,日趋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最佳出路。
“想办法让老师记住你”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严嘉萱搜集了几乎全县所有985学子们关于“保研”的建议,初步明白了保研规则“分看考试成绩和竞赛科研两个方面”。大一入学没多久,她就从校园网上下载了学院这一年度的保研细则,条分缕析地研究了各科绩点的具体算法、科研竞赛的加分规则、加权总成绩的排名方式。而每年的保研细则,也成了严嘉萱前三年大学生活中的行动指南。
按照她的规划,她在大一就加入了一个学长组建的科研团队“抱大腿”——帮忙做些议程记录、打印资料之类的琐事,从而在最终成型的论文上挂上了自己的名字,拿到了第一个竞赛加分。
严嘉萱准备的保研资料
她也从学长那里了解到,对人文社科类学生来说,每门课程的阅读报告、期中期末论文对最终的成绩有多重要。于是,从第一门课程开始,她都会在作业上交周期的第一天提交作业,如果是五千字的作业,她会写到八千字,还会贴心地附上目录、注释、参考文献、页眉页脚。虽然作业内容,仅仅是某本书的读后感;但形式上的郑重其事,能向老师们直观展现她有多么精益求精。
作业字数的内卷普遍存在于可以保研的各大高校中的各个专业——毕竟这是最容易仿效也最易于操作的抬高“印象分”的方法。在某双非一本读本科的刘念透露,同学们会把五千字“卷”到八千字、一万字、一万五千字,绞尽脑汁去拼凑对一个简单问题的长篇大论。字数抵达极限后,大家又开始寻求“形式上的创新”。最终刘念想到了一个可以脱颖而出的方法:在上交的每份作业后面附上自己的查重报告,以证明这一万多字都是自己的原创,而非复制粘贴。
抬高“印象分”最关键的一点是,想办法让老师记住你。
同样就读于某双非一本的张妍总结了几点和老师熟络的办法:首先,类似于“思修”这样公认的水课,大家的上课态度普遍比较消极,会坐在教室后面玩手机或者做别的科目作业;而她总是坐在第一排,和老师眼神交流、积极互动——虽然这些课程在某种意义上毫无价值,但它们却是占了三到四个学分的必修课。除此之外,她会积极地担任各科课代表,因为这是大学里和授课老师接触最频繁的角色。如果没能成为课代表,她就在下课后围住老师问问题,但大学里教的知识都太简单了,根本没什么好问的。更多时候,她需要花费心思去“制造”一些看上去动了脑子、还有点儿难度的问题,虽然她对这些所谓问题的答案丝毫不感兴趣。
但张妍最终以0.01分的差距与保研名额失之交臂后,有同学对她说,有些水课她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折,大可以直接对授课老师说,“我要保研,请您把分数打高一些”。
张妍的期末复习资料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地让老师认识自己。严嘉萱刚刚跻身沪上名校,面对光怪陆离的大城市,内心充满了自卑与畏惧。她像是得了“潮人恐惧症”,看到校园里打扮入时的同学,不由得敬而远之。她不敢和老师互动,只好埋头把作业完成得更加精致,把每一科期末考试范围内的题背得更加滚瓜烂熟。
“我希望老师给我高分是因为欣赏我的学业表现,而并不是因为我刻意去和老师搞好关系。”她质疑这种竞争方式的公平性,也同样质疑通过所谓“社会实践”换得保研加分的行为,“在我看来那种东西就是随便立个项,然后做个花里胡哨的PPT、项目书放上去,大家心知肚明——老师知道你是为了啥,你自己心里更清楚,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没有意义。”
她能抓住的,就是成绩。在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她就着手开始复习,每一门课程她都至少背诵四遍,确保万无一失,“如果有一门3学分的专业课考差了,可能就和保研彻底绝缘了”。张妍就曾有一门专业课的成绩遭遇滑铁卢,这让她剩下的大学时光全用来亡羊补牢。大二那年,她因为忙于志愿服务社团的工作,一门4学分的“大学物理”只考了七十多分。本来绩点领先的她被拉低了0.3分,不得不抓住之后的每一次考试“填坑”。
张妍的期末复习资料
几乎所有人都使尽浑身解数抬高自己的成绩,所以很多专业,几十个人,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可能只有5分以内的差距。要想拉开分差赢得那仅有的几个保研名额,需要在科研论文、各类竞赛、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都有所斩获,像集龙珠一样集齐所有的荣誉,最终召唤出一个保研名额。
大三那年,张妍花了几千块钱“版面费”,通过中介在某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按照往年的保研规则,她可以得到一分的加分——这一分,就足以让她超越十几个人。而从大二开始,刘念就频繁地参加各式竞赛:演讲比赛、礼仪之星大赛、“互联网+”创意策划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全国数学竞赛……但始终没能获得一个可以保研加分的成绩。直到上交保研材料的前几天,老师告知她所参与的某节能减排方案竞赛获得了全国三等奖,这个级别的荣誉可以获得的加分,让她从保研边缘人一跃成为学院前五名。
虽然严嘉萱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她依旧为此焦虑。如果单纯看专业课成绩,她几乎可以达到满绩;但算上思政类课程以及各类加分,她只能排到班级30%左右,徘徊在保研线的边缘。
大一下学期,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男友的父母都是另一所大学的教授。她发现男友暑期可以随意去到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实验室实习;参加各类学术竞赛,带队老师也总会跟男友的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师生关系。这些在严嘉萱看来遥不可及的资源,男友全都唾手可得。那时她逐渐明白,这场名为“保研”的游戏,所有人从一开始就站在完全不同的起点。
对手
因为保研名额的竞争,严嘉萱觉得,大学四年,同班同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比较疏离。跟她关系最好的除了男友,就是上一级的某位学长——学长保研去了她心仪的专业,可以传授给她详尽的保研攻略。

这种现象也并不罕见。在张妍所在的学校,到了大二,班级里入围“保研圈”的几个人开始崭露头角,相互打探对方参加了什么竞赛、有没有什么科研项目。张妍也会时常登录各类竞赛的官网,搜索班级里几个竞争对手的名字,看他们有没有获奖;再按照保研细则计算出他们的加分,确认自己的排名。到了大三,这场没有硝烟的漫长战事愈发激烈,她发现“保研圈”的几个人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彼此冷漠地擦身而过。大三暑假,她和同班一个女生都入围了北京某高校举办的保研夏令营,她们没有联络对方,各自从学校来到北京。开营仪式当天,张妍走上前去问那个女生,分酒店的时候要不要住在同一间。对方不置可否地微微笑了笑,转过身去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攀谈起来。
这种暗中较量的敌意如果不被约束,就会演化为彼此伤害的阴暗行径。就读于某著名211院校的乔婷透露说,他们学院某个班级绩点排名第一的学生,利用某专业课收作业的职务之便,肆意篡改全班其他几个有保研资格同学的作业,以便让自己获得更为稳妥的优势。事情败露后,其他几位学生联名向学校检举,他们最核心的诉求是,一定要剥夺这个人的保研资格。这一事件后来在某社交媒体上发酵,引起轩然大波。许多网友在下面竞相分享本班同学为了保研伤害他人的做法:侵入校园网修改竞争对手的实验课成绩、学习委员故意给全班传达错误的考试范围、奖学金民主选举作弊等等。
刚刚从某985高校毕业的陈梦涵,见证了班级里的前三年形影不离的两个女生,因为争夺一个保研名额而分道扬镳、相互诋毁。她记得,大二那年,疫情暴发了。那年的毕业季,似乎所有信息都在渲染疫情之下极端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考公考研人数再创新高,出国读书也变得遥不可及。保研,成为他们这一届学子毕业出路的最优解。
为了成功保研,陈梦涵的大学生活基本都是在上课、泡图书馆。因为怕耽误时间,她没有参与任何社团活动。对于自己的专业,她说不上热爱,仅仅是不反感而已,“我想读研就是因为想提升自己的学历,以后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对于学术的追求,根本谈不上。”
但到了最后时刻,陈梦涵所在学院修改了保研政策,她原本的一个省级竞赛奖项被取消了加分,最终以两名之差没有保上。她和另外一些失败的同学去质问学院老师为什么临时调整政策而不提前通知,老师烦躁地回复,谁说没有提前通知?不是让那谁跟你们几个保研圈的人说了吗?陈梦涵这才意识到,和她一起参加暑期保研夏令营的“那谁”、她视为推心置腹的好友的“那谁”,原来早就知道保研政策调整的消息,只是一直没有告诉她。
“保研失败给我的教训就是,首先身边的人都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其次,做人还是要社会一些,要和老师多多沟通来获得一手信息。如果你想要达成这样一个结果,就要学着功利一些。”陈梦涵说。
自残
背负着一定要保上研的巨大压力,严嘉萱从大一就生活在一种极度焦虑的情绪之中。
她对思政类课程毫无兴趣,也无法参与一些表面光鲜的“社会实践”项目,但又会面临强烈的自我审判:她仿佛幻化成两个自我,一个在谴责自己总是躲在“小镇做题家”的舒适区里,丝毫不敢挑战和克服自身局限性;另一个又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有自由有权力做真正认可的事情。在这种反复拉扯中,严嘉萱筋疲力竭。
大学生活相较高中清闲太多,没了一个月一次的阶段性模考,严嘉萱觉得平时的生活虚无又空洞;但这四年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保研,而每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都会左右这个最终的结果。因此,每个学期末她都会特别暴躁易怒。
有一年元旦前后,她和几个朋友创业卖学校的文创周边,订单配送出现了问题,需要他们解决很多非常琐碎的事情,又正好赶到期末考试季,严嘉萱觉得压力全部向她涌来。一个阴沉的黄昏,她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着班级群里刚发布的考试安排,感觉头皮发麻、全身不停颤抖,那时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从楼上跳下去,摆脱现在的一切。
为了不让自己自杀,她拿起手边的美工刀去割桌上的橘子皮,切割的畅快感让她觉得解压。接着,鬼使神差地,她把美工刀伸向了自己的手臂。
这次自残没有让严嘉萱受伤太重,但从此之后,遇到类似急躁抓狂的时刻,她都会用自残来纾解压力。
大二的时候,疫情暴发了。严嘉萱在家里上了一个学期网课,那个学期期末,学校把考核标准从线下考试改成了线上提交课程论文,而写论文的那段时间,严嘉萱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在过去,她所习得的所有学习技能都是熟稔地掌握某些知识,然后用它来完美无缺地满足某种客观评价标准:比如把考试范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在考场上奋笔疾书。但写论文不是这样,她无法揣摩老师的评价标准,不知自己的选题和写作是否投其所好。她甚至怀疑自己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毫无意义,她想到如果读研,那还需要再花上三年时间去写这些东西。
第一次,她开始质疑自己是否适合读研,以及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
回到学校,严嘉萱开始重度失眠。她质疑保研的意义,但做题家的惯性又无法让她彻底放弃。她整夜整夜地失眠,但到了白天,又没有能量从床上下去,因为一旦清醒,就要面对一个被精准量化的世界:课程的绩点、论文的等级、竞赛的奖项、志愿服务的工时、社会实践的荣誉,学校里所推崇的“人生赢家”,甚至连身材外貌、恋爱对象都要完美。从床上下来后的每一天,她都要奋力去满足这所有的评价标准,最终让自己抵达理想的彼岸——保研。但她心里分明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严重的失眠和焦虑让严嘉萱长期晨昏颠倒、精神恍惚,行动力下降。大三下学期,当所有课程考试结束之后,她的痛苦达到了极点,因为所有可以努力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发力的机会,剩下的只是被动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自杀的念头再次浮出脑海,严嘉萱主动去看了心理医生,她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看到诊断结果,她马上像逃生一样收拾东西回了老家,逃离了被她看作内卷中心的学校。
游戏规则
大三暑假,还在河南老家的严嘉萱得知了她保研失败的消息——就在这一年,教育部修改了直属高校的保研规则。按照新规,从大一就参与科研创新类竞赛的严嘉萱只能挑选所获荣誉中最高的一项去加分,而不能将连续三年的科研荣誉全部加分。这导致她以两名之差无缘保研。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严嘉萱有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但她还是无法接受三年多的努力全部落空,回到学校后,她找遍了学院教务、副院长、院长甚至投递了校长信箱,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为自己换来一丝转机,但“学校像踢皮球一样把责任推给各个部门”,她最终没能争取来自己想要的结果。
并且因为她的持续投诉,受惠于新政策而榜上有名的保研生对她群起而攻,她的防御方式就是在班级中更加沉默疏离,“反正大四了,大家各干各的,毕业后就彻底相忘于江湖了。”
同班同学对严嘉萱申诉保研政策这一行为颇为不满
张妍同样因为保研政策调整而落败。在出保研名单的前几天,学校突然通知会议论文的加分取消、只有期刊论文能够加分——这导致她花了好几千块钱投递的那篇会议论文变得毫无用处。“可能学校也觉得我们双非本科生写不出什么高水平论文来吧”,张妍无奈地说,如果提前一个学期学校通知政策调整,她还可以再冲一冲竞赛加分。可提前几天通知,她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
保研失败让当时的张妍极度痛苦,室友们轮流陪了她好几天,担心她因为想不开出现意外。因为情绪起伏太大,她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但这也让她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热爱学习和科研,“我只是害怕失败,接受不了考不好、接受不了保不上研、接受不了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她最终决定去一家企业做管培生,她觉得这次失败教会她比得到一个保研名额重要得多的事情:如何善待自己,如何真正地爱自己。
在某985高校读冷门文科专业的陈梦涵也受到了保研政策调整的影响。院系回应说因为国家强调更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加大了学年论文成果的权重,“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实隐晦的含义就是看谁更能经营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以一名之差落败的她也去找学院申诉,“他们甚至直接承认今年系里的保研政策是有问题,明年会改回来,但今年就这么着了。”因为频繁地去和老师面谈,校内BBS开始流传,说某院系女生每天去找教务老师哭诉哀求一个保研名额的故事。
保研失败后,陈梦涵尝试去找工作,还去参加了国考市考,最终通过考研上岸。短暂的求职经历让她明白,要是想考上公务员,必须要有当班干部的经历、要获得优秀班干部的奖项、必须要是党员;要是想进大厂工作,就要多积攒实习经验,抱紧实习期间领导的大腿,争取内推。陈梦涵开始计划着在新的人生阶段,如何开启新一轮的“集龙珠”游戏。

严嘉萱则用疯狂看韩剧来疗愈,韩剧《鬼怪》里的一句话让她潸然泪下:
“神没有安排任何人的命运。你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只是神向你提出的问题,而你的行动本身就是解答。”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让我保不上研,可能是上天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就要用我的行动去解答它。”想在研究生阶段转读教育学的她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反思“小镇做题家”这个身份:“从小到大的生活模式就是一周一小考、两周一大考,不断的阶段性目标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所以不论做什么,我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一旦失去目标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但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闲暇、如何享受自由,所以都是一边焦虑一边愧疚一边摆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生活本身才是我最应该珍视的目标。”
大四那年,她加入了吉他社团,和朋友们组乐队演出;她还加入了脱口秀社团——在此之前,严嘉萱从没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爱好。她和男友分了手,尽管在她爸爸看来男友一表人才,但严嘉萱觉得他“就像韩国电影《寄生虫》里那些上流人士一样,精致又伪善”。
尽管周围很多人劝她考研,但严嘉萱最终选择去北京的一家媒体工作。她已经厌倦了校园里对于“优秀”的评价标准,“如果我真的关心具体的人,就应该去真实的世界看看。”
她明白,走入职场、走进“大人的世界”,又有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对“人生赢家”有了新的评判标准和衡量尺度。但这一次,她不想再把自己放置在任何竞技规则之中,她想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