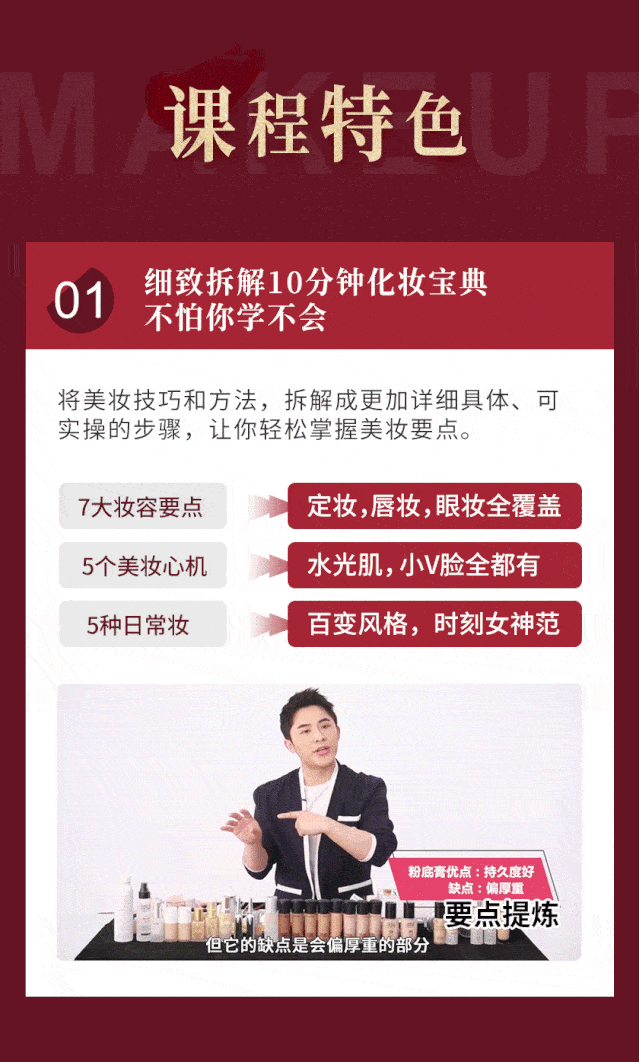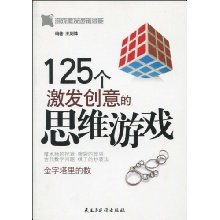和耳东尘相识,始于我先前在中国国家地理工作的经历。耳东尘是那种所有地理类图片编辑都梦寐以求的合作对象:第一时间提供具有准确的文化特质,同时又饱含温度的照片。如果做到广东相关的选题,我第一个想到的摄影师就是耳东尘。
这篇对话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次交流。人文记录几乎是所有摄影师都会触碰到的题材——只要你在人群中生活、观察、行走。然而,长期聚焦某一种特定的文化主题,十几年如一日坚持拍摄,逐渐形成自己的影响力,并围绕同一个文化主题不断创业,获得了持续性的商业回报——能做到这些的摄影师不多,耳东尘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也想投身于所热爱的文化记录中,并且做到投入与收益上的良性循环,希望这篇对话能给到你一些启示。
耳东尘
本土文创品牌“大写岭南”联合创始人
中国国家地理合作摄影师
GettyImages图片社签约摄影师
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
广州西关传统民居:西关大屋。耳东尘常年致力于拍摄岭南地区的传统文化题材。
对 话
主持人:Geethan
访谈嘉宾:耳东尘
辍学学摄影:去学一技之长,养活自己
G:虽然有很多关于你个人经历的公开报道,色影无忌希望能在这里还原一个完整真实的你。请先谈谈你个人的成长经历吧。
耳:我1981年出生在江西中部的一个小县城。家人比较多,我排行老六,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小时候,我爸在乡镇单位工作,很少回县城,每一个月回来一两次。我妈就带着全家一帮小朋友,我几乎是放养形态,就是那种山里面跑的野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关系都非常好,我爸知道我不爱读书,说我只要不干坏事,不杀人放火,做啥都可以。
G:兄弟姐妹几个人,后来有做跟你相似职业选择的吗?文化艺术相关工作的。
耳:没有。
G:也就是说你们家的摄影基因是从你这里开始的。
耳:对的。误打误撞就学了摄影。
G:怎么开始接触摄影的?
耳:1997年我初中毕业,本身是个学渣,不爱读书只爱玩,我爸就让我去南昌一所职校学工艺美术,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唱歌跳舞这类偏艺术的东西。结果我去了以后连一个苹果都画不了,后来就辍学了。
辍学那年,我18岁。当时在南昌租了个房子,住的地方隔壁有几个学长开了间影楼,这在当时来说是件很潮的事情。他们会穿烂牛仔裤,学香港那边打耳洞,染头发,那个时候很酷,现在来看应该算杀马特。
我经常去影棚玩,一来二往就正式拜师学艺。那时候学手艺,才真正的是学手艺,从做人做事开始,师父干活,就在旁边做些杂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第一台相机时,每天钻研各种参数和技艺,买各种专业类的摄影杂志,泡各种专业论坛。
G:专业论坛?看色影无忌吗?
耳:是的,我是无忌忠实粉!
G:在这段经历中,你如何理解摄影?
耳:当时我觉得摄影就是我一张饭票,我去学一技之长,然后能够养活自己。完全没有对摄影艺术、人文纪实有后来这种深刻的感觉。只是想学好一门手艺,回老家开个照相馆,和大家学炒菜、学木匠、学开挖掘机是一样的。
G:之后你进入了商业摄影的领域,正式开始了摄影的职业生涯。聊聊这段时期吧。
耳:学艺之后和我二姐在南昌开了家小照相馆为生,在一所大学旁边,给学生拍毕业照之类的,很基础的工作,开了三年。我离开以后,我姐又坚持了四年,应该算老店了。
G:2000年,你为什么去了北京?
耳: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住在相馆里面,觉得每天生活很枯燥,很单调,人在慢慢长大,想法是会不断开阔的,觉得摸到天花板就去北京进修了,我把我所有积蓄全带去北京了。觉得北京是全国中心,想在那边学一技之长,成家立业。
在五棵松那边,我给学校交了很多钱。学校给我教学材料,我一看我全都会啊,我还交那么多钱干嘛呢?但是校方还不给我退,我就改专业,学了一年的化妆,拿了个中级化妆师证,还在北京当了半年的化妆师。
G:2002年,你又为何选择南下广州?
耳:因为我不是北方人,北京的冬天超级冷,我也很怕冷!那个时候很穷的,我和朋友住在岳各庄,租了一个很便宜刚刚盖好的房子,没有暖气,身上也没有钱,还老流鼻血。当时我四姐在广州工作,我问她那边怎么样,她说我就穿一件衣服!我说天呐,我就投奔你吧!然后我就从北方的茫茫大雪来到了南方的春暖花开,好幸福。
2002年,刚到广州时的耳东尘,曾经也是摇滚味十足的小鲜肉一枚。
耳:2002年来的广州,待业了一年。我当时给广州所有影楼都投了简历,没有一家公司要我。我后来寻思为什么没人要我,发现是我的简历写错了。我在简历上写我会化妆,会摄影,会美工,会后期,他们就觉得你一个小屁孩,怎么什么都会?后来我就只写我会摄影,就找到了工作。第一份工作拍老年婚纱照,连锁婚纱,做得挺大的,叫夕阳红。我每天也是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G:感觉回到了你在南昌时的那种生活状态。
耳:对,每天早上外面排了一堆老人家,“下一位!”开门关门,跟大夫看病一样。所有的灯光化妆造型,都是一模一样,拿一个胶片机哐哐哐拍,拍完分片。经常有老人家拿错放大的照片,因为化妆服装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就是为了生存,活下来很重要。
G:你从一名拍摄老年婚纱摄影的摄影师如何转型为一名真正的广告摄影师,对你而言,这段经历带给你什么?
耳:一年以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广告摄影公司,我就想考虑换一个行业,就去做了摄影助理。
G:相当于又是从零学起。
耳:对,广告摄影和影楼摄影完全不同,慢慢就开始涉及布光、器材,根据接到的活调整布光和各种参数。
我开始尝试去拍杂志选题,比如拍教别人做面包、做菜、插花。半年、三个月,拍一套书。像拍那种食谱类的书,给人做汤,365天365种汤,每天要等到人家店晚上九点打烊,师傅才有时间出来拍东西,我们就晚上开工,拍到凌晨。
当时用的相机也是大画幅的座机,非常专业的。那时老板每天允许我把座机拿回家,因为我第二天要直接去现场。回家以后我就不停地拆、装、拆、装相机,后来干脆关了灯拆装,就像那些士兵玩枪一样。后来我闭着眼就能把相机装起来,调整参数。
G:这一阶段,你如何理解摄影,相较之前有什么变化?
耳:这份工作真正是最锻炼我技术的,让我对摄影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让我知道摄影不仅是拍人像、拍毕业照。收入也比之前拍影楼高一点,接触的摄影门类也更广。我拍杂志,跟着他们出去采访,可以接触更多的行业,了解不同人的故事。
G:商业摄影的这段经历,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耳:商业摄影最大的价值是帮客户呈现其诉求和想法。对于我的影响就是每完成一单自己累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解决方案。熟练的技术对于每一位摄影来说是最容易达到的,但是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需要无限多的案例来累积,完成一个职业摄影师的修炼。
耳东尘和搭档史丹妮。
G:后来为什么去了《生活元素》杂志?
耳:在广告公司干了两年,太辛苦了,后来我离职,自己开了工作室。但问题是,自己没有客户资源,偶尔一两个月来一单,没有资源,哪怕技术再好也没用,房租也交不起。后来我就想去媒体看看。2004年那会儿,传统媒体平面媒体很盛行,像周末画报、广州日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自媒体。我又是投了全广州所有的媒体,包括内刊,但没有一家要我。
G:这个经历似曾相识。
耳:对。我就把资料放在智联招聘上,后来有一天突然接到《生活元素》的电话。当时一起竞争摄影师职位的有鲁美、北影毕业的,后来经过三轮面试,最后选择了我。面试的题目是去面包店采访,拍一个面包,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就老帮别人拍怎么做美食。我自己带着灯光、器材、摄影布,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拍摄地。最后我的作品打动了主编。当时那个面试我的主编,就是我现在工作室的搭档,史丹妮。
G: 在《生活元素》这个媒体平台,给你带来了什么?
耳:在媒体的那三年,对我的价值观和认知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生活元素》定位做高端生活方式,采访豪车、豪宅、奢侈品等,当年做得非常棒,华南地区第一吧。期间接触过很多品牌,比如法拉利、玛莎拉蒂、宝马、路虎、欧米茄、莱佛士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洲际酒店、香港旅游局、三亚旅游局、保利地产、雅居乐地产、汇景新城、方圆地产、颐和地产、颐和地产、伊莱克斯、长隆集团……
那时候起,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更高的阶层,是普通百姓可能摸不到的阶层。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去试驾法拉利,怎么可能免费住五星级酒店,去到某些地方,还有当地的旅游局招待。
文化的传播者到创业者:做自己喜欢的事
G:累积了这么多经验和商业人脉资源,你却开始转投文化记录摄影,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驱使你做出这样选择的初衷是什么?
耳:在媒体的那段时间,每天上班采访的是高端生活,出差出入的是高级酒店,下班后还是得挤公交、去菜市场买菜等,觉得跟现实生活差距太大,有点分裂。当时在媒体工作会做很多采访,采访对象也会有一些人文领域的艺术家,画家、建筑师都有。采访时能听到很多真实的故事分享。相比去采访房地产商,我个人更喜欢去进行这样的采访,自己本身也一直喜欢传统人文的东西。
后来正好有了一个契机:2008年,我刚刚结婚,马上小孩也快生了,我觉得这份工资可能养不活我的家人,而且这份工作也没太多上升空间,如果一直做下去,我能看到十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离职了。
G:你在这个时候出去创业,家人支持你吗?
耳:支持,他们一直到现在都很支持。虽然到现在都没有很富裕,但我家里人,我太太,我小孩都非常支持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做人文摄影创业其实很难的,像我们做了12年。如果你12年了,还是像当初一样,没有一个质的飞跃,一般家里人早叫你放弃了。有时候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我一方面是和自己斗气,一方面也是做给家里人看,你看我做这个是行得通的。
那时正好史丹妮也离职了,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公司的价值观有些不合。后来我们在一个项目中又遇到,一拍即合,就想着一起做工作室,平时拍广告,然后同时记录生活的这片土地。
G:之前和你聊过,你提到做岭南文化,是史丹妮的乡愁。她是广州本地人吗?
耳:对,她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广东人,她从小在广州长大,对广州的感情比我深太多了。于我而言,生活在大城市,每天车水马龙,住在水泥房子里面。偶尔去郊区拍拍人文,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吃农家菜,拍老房子,就跟我以前小时候差不多嘛,因为江西有很多明清古宅,村子里也是很质朴的感觉。
在岭南文化的记录中,我看到一种神奇的冲突与融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广东,古老的屋宇、风俗、物产,都好好地还在,这种冲突,常能使摄影作品有很强的张力和戏剧感。
广州文明路。
G:我们先聊些关于面包与现实的问题。工作室一开始的运营情况如何?

耳:其实工作室成立刚开始,最大的阻力是如何活下去。刚开始是一半时间接商业单,养活自己和团队,一半时间下乡采访拍摄。很大一段时间里为了糊口,做很多商业摄影,后来发现不对,我们一直这样做下去,有没有作品留下来,有没有为这个城市留下点什么?
从这个问题出发后,我们于是决定慢慢断了自己的客户关系,留更多的时间创作,从岭南深处走下去做人文记录,一做就是12年。12年来大家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默契,史丹妮对文字和图片的编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工作室的文字和图片编辑都是史丹妮主导完成。不用多说都能明白彼此的想法和构思,做就完了。
G:能概括下自己的创业经历了哪些阶段吗?
耳:主线一直没变,就是记录岭南文化。但同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广告、商单,以前积累的很多显赫的客户名单,就是为了生存。我和史丹妮做这个工作室,有几类客户是一定会接的:第一是奢侈品品牌,因为它们让我们的简历好看,收入也不会差。第二种,你不是大品牌,但创意想法全部让我来出,我也会接,这样我能积累出真正的作品,而不只是钱。
我也一直在跨界做美食、做设计、做策展等,一来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二来在狭窄的摄影赛道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腾讯大粤网颁了“2016广州十大跨界生活美学家奖“,二更广州颁发了“2018更广州年度人物奖”给我,也算对我这么多年跨界的认可。
耳东尘在珠江4K频道《拜托了,大厨》第一季。不会做美食的摄影师不是好的跨界生活家。
我们创立了以岭南文化为主体的文创品牌“大写岭南”,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得到了很多客户和粉丝的喜爱。从给客户拍摄商业摄影到给客户定制文创礼品,经历了太多披星戴月的艰难。
“大写岭南”设计的手作灯笼,模拟出月亮透过旧时花窗铺在屋内的美感。
近年我们一直在帮政府做文化出版,出版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我们现在帮广州市园林局、广州市国规委、广东省文物总局出一些介绍广州的画册。我去年帮国规委出了广州历史建筑的几本书,把广州市所有的历史建筑重新拍了一次。今年在做省文物总局的一个出版物,是做广东省的文物古建的一个出版。
整个出版,我们从策划、设计、拍摄到制作都是我们工作室全部负责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摄影策展和版权交易。随着大家对版权意识的重视,我们多少能有点微薄的收入,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2021可能会有新的尝试,比如做岭南文化展厅、数字化平台等。
“大写岭南”团队为政府做的出版物。
G:成立工作室这些年,你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否一直清晰?
耳:对,一直很清晰。做岭南文化这件事,其实是苦乐参半。有些快乐只有我们自己能体会到。虽然这么多年公司也没做到几百人,还是那么个小公司。但还是那句话,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商业广告和文化出版项目够养自己和工作室。我和拍档史丹妮都不是野心太大的创业者,能体面地活着,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人生已足矣,不敢奢求太多。
G:之前你开过一家叫做食间站亭的餐厅,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后来为什么关门了,遇到了什么困难?
耳:我们白天做工作室、拍照片很辛苦,而我平时也喜欢自己做菜。我当时就把一间影棚拆了,做成了厨房,几百方,很专业的厨房。因为我们在创意园里面,租金还比较低。我们每次采风,除了拍东西之外,我会把当地的食材和特产带回工作室分享给朋友,我觉得做饭的整个过程很解压,什么都不用想,是一个享受当下的过程。
城市人每天最苦恼的就两件人生大事: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于是我就在工作室附近找了一间小店,20平方,做了一个类似深夜食堂的那种餐厅,就是食间站亭,专门供应健康的、有广东各地特色的快餐。我们每天去菜场买菜,也绝不用冰冻肉、地沟油,跟我自己家里吃饭一模一样。食文化在广州很重要,和大家分享,原来清远、湛江、阳山有这样那样的食材。这是我对于传播岭南文化的一个新的尝试。
这个店后来慢慢变成网红店,通过它认识了很多朋友,做过很多节目。后来我们从20平方搬到了200平方的双层,正要赚钱的时候,疫情来了。2020年二月,我们几个股东开会,我说要立马关张,千万不能拖着,不然亏得更惨。纯粹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失败案例。
G:那如果有机会,之后会不会重新开张?
耳:可能不会开后来这种规模的了。餐厅这种东西,做得小还挺好玩的,但做大了,你就要开始管各种事,人员啊,菜品啊,采购啊,研发啊,给大厨教学啊,会耗掉我很多精力,影响我做岭南文化采风的主线。以后再开,可能我就去深山老林里找个地方。
但是我“耳先生杂货铺”的项目还一直在做。
G:耳先生杂货铺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耳:大写岭南是精神上的,食间站亭是食欲上的,杂货铺就是玩物,生活形态、生活方式的东西。我经常在朋友圈晒自己买的东西,很多朋友就说让我帮他们挑东西、买东西。有一天我就在朋友圈发着玩,说我要开一个杂货铺,大家赶紧给我打钱。结果那天晚上我的微信就收到了总共十万块钱。我很多粉丝,就直接给我打钱。
G:日挣十万不是梦。
耳:然后我就去做众筹,筹了100万。之后我又租了一间小铺子,卖这些生活中吃喝玩乐的好玩物件。生活装备、衣服、欧洲100多个小众品牌的生活好物。
G:实际上你在给你认可的一些品牌,搭建了一个平台。像网易严选,你这是耳东尘优选。
耳:对对,经过我推荐的东西,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一个小工作室,自娱自乐。很多摄影类和生活类的品牌,也会拿给我进行评测。
深耕岭南文化:接近真实的自己
梅州丰顺,舞火龙
G:我们回到摄影的话题。你给我的感觉,绝不是一个只顾闷头拍照的“老实人”形象——去TED演讲,去各大卫视做主厨分享、美食直播,作品参展各种摄影节。你甚至还在做一些装置艺术项目。包括为政府策划出版项目、为客户设计文创产品,种种这些事情占据着你的时间和精力,而你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体的曝光和关注。
在种种身份的交织中,你的心态是否经历过浮躁?是否对你的岭南人文摄影工作本身产生负面的作用?
耳:不会,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加分项。人文摄影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比方说我会做菜,到乡下以后我就会和这些大妈学做菜,我餐厅很多菜是我从乡下学回来的。史丹妮的婶婶在乡下,她就教过我做鹅。这种和乡民之间的互动很美妙。
再比如说我们研究过米的100种吃法,南方吃米和北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人文摄影研究的一个分项。摄影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种记录,拍人文纪实涉及到很多不同门类的知识形态,建筑的形制、植物的分类、食物的特点之类,不能光拍而拍,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G:你平时是怎么积累知识的?
耳: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结交各行业的痴者,从跟他们的交谈中受益,再去找相关的书籍和知识去巩固学习,再互相交流。
说实话,这么多年一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野采风,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很少跟摄影圈交流,反而跟其他圈交流多,比如艺术、设计、建筑、美食、生活美学圈等。在其他圈子吸收营养,反哺摄影门类上的不足。老在摄影单一的圈子里打转,我会觉得很闷。
PechaKuchaNight分享会, 耳东尘在现场分享拍摄体会并与茑屋书店设计师交流。
G:这一阶段,你如何理解摄影?
耳:摄影于我,慢慢变成一种手段、一种媒介。摄影是一个和人交流、对生活进行探索的敲门砖。
G:在人文摄影创作的领域中,有你欣赏的人吗?可否具体举例?
耳:有。比如薇薇安迈尔,那个保姆摄影师,她厉害的地方在于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可能当下看是没什么意义的,但很多年后看起来会很打动人,因为它记录的是生活最真实的状态。还有香港的何藩,他的用光、构图的简洁的风格是我喜欢的。
身边的人,我非常敬佩的一个广州老人,李瑞然。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90岁,佝着个背,背着台尼康,在拍街拍,我好几次碰到他。我在车展也碰到他,在拍美女。后来有网络媒体联系我,问我有没有拍过老人的肖像,要为他做一个纪念册,那时我才知道这个老人有多牛。他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发现几十箱胶卷没有洗出来,因为没钱去洗,后来就捐给档案馆了。他就是一个广州本地的摄影爱好者,几十年如一日记录城市的变迁,最厉害的地方是会给照片归档、分类,比档案馆还齐全,我觉得他干的事情太牛了。他就是一个无名英雄。
G:关于文化记录摄影,这些年你拍摄数量最多的题材是什么,你和团队平时会做哪些准备?
耳:12年来主要拍摄岭南地区的村落、建筑、人文、美食和植物。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生活形态记录。
我们主要会先研究村落的历史和生活习俗,比如哪些传统节日会有些什么传统的习俗、哪些村落有历史有故事的建筑、哪些植物那些人会迁徙于此等等,会先考证,再踩点,最后再深入的采访拍摄。这些年,我们去过开平、阳江、清远、连州、潮洲、汕头、揭阳、肇庆、东莞等等各市,以及这些城市和广州市周边的许多乡镇。
顺德碧江金楼,木雕艺术。
G:你最满意的作品是?
耳:其实每一处乡村、每一座建筑都有不一样的故事,都让人印象深刻,我其实更喜欢建筑里面的人,让我们很真切感受到城市里久违的——人情味。
要说最喜欢,一个是我在顺德拍端午龙舟,太公分猪肉的那张。龙舟我们拍了五年,还去巴黎做过展览。龙舟在广东各个地方有不一样的习俗,那五年我们基本把这个习俗都记录完整了。我喜欢分猪肉这张,当时我在一旁拍照,他们就给我吃肉,那时我有史以来吃过最好的一块烧肉。
顺德端午龙舟,太公分猪肉。
耳:还有一组照片,我也非常喜欢。是讲珠江新城村落拆迁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当地人每年比完龙舟,会把龙舟藏在泥塘里面,第二年端午再把龙舟翻出来。珠江新城石牌村、冼村拆迁,村民的要求就是,你可以拆我的房子,但你要保留藏龙的那条河冲。
后来,石牌村没有保留藏龙塘,但保留了祠堂。于是村民把龙舟放到黄埔双岗村的表亲那里,端午时节再挖出来,顺着珠江口进到珠江新城,去到祠堂里祭拜。那种新旧对比的感觉很奇妙,时代在进步,但还是会留给你一些质朴的传统,这才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2012年,石牌村端午龙舟。
G:你如何看待文化记录摄影的价值和对你的影响?
耳:我拍摄的许多建筑、习俗都在慢慢地消失或变化,自己拍摄的目的,好像也从一开始对形式感的追求,到后来代入使命感的记录。
文化记录的价值可能不是当下的价值,而是10年20年甚至50年之后再回看这些影像和文字,才对当时当下的生活形态有研究和记录的价值。特别在城市化进程的当下,很多建筑和习俗都在消失和摧毁,作为摄影师最重要的就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下,记录这个时代的断层。对我而言,会更关注当下生活趋同的变化。
从化麻村,2019年。以前这个村非常非常大,多是祖屋老房,年久失修,没有人住。红色区域为近年来当地农民把老房子拆掉后盖起来的瓷砖两层的别墅,蓝色瓦顶。
G:你如何理解摄影作品中的艺术性?
耳:是不是艺术对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真实的当下,才是我关注的焦点。蒙娜丽莎的微笑和农民丰收的喜悦,在我看来是一样温暖的。
G:十二载记录岭南文化,在常人看来已是一段足够漫长的时间。你是否会觉得这样的拍摄会显得乏味和重复?
耳:不会重复,岭南太大了,估计等我死了我都走不完。我们拍摄的题材很多,每次都有新鲜感。
G:为政府等机构做拍摄和出版,本质上是一种劳务行为。你在完成这样的拍摄时,如何平衡人文摄影的创作动机和政府作为甲方的实际需求?
耳:来找我们的其实都是看中我们自己的才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干预和改动。我们本身做这件事,也是要尽量去当成一个作品去做,而不是一个商品。过几十年再翻看我们做的书,不会说想把它扔掉,不想看。很多时候因为有政府的委托,会给我们的拍摄带来更大的便利。我们去年拍摄了广州很多古建,一般人只能在外面拍拍,但我们就可以有专业人员领着我们进入到内部拍摄一些隐秘的结构,这对我来说也很开心的啊。政府的委托其实对我们的拍摄是一个提升的作用。今年我们又会去拍很多广东省的古建。
G:记录岭南文化,是否就是你全部的野心?有没有考虑过去记录一些其他地区的文化,例如你的老家江西的赣江文化,还有徽派文化、晋商文化等等。
耳:没考虑过。有的虽然喜欢,但不太熟。而且跨着文化地域,很多东西又要从零开始,需要重新建立感情的连接。时不我待,我都快四十了,有的时候我也想早点退休。
工作中的耳东尘

G:经历过商业、媒体的阶段,直到今天这个阶段,你现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是一名纯粹的摄影师吗?
耳:我现在一直在跨界,说得好听是跨界,难听点就是不务正业。我其实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摄影师。我喜欢玩乐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专门去做一个人文摄影师,又养不活自己。所以可能需要十八般武艺吧,让自己变得更强大,适应这个社会。把对方熬死,而不是打死,活下来最重要。至于以后,理想和抱负,每天坚持就Ok了,至于有没有太多的回报,我随遇而安。
去年六月,我外婆走了,九月我父亲走了。这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之前我经常会和父亲说我在做的事,而现在项目做得更大,却无人可说,缺少了一个出口。以后会更加内观自己的内心和家庭吧。
G:以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作为基点,将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角色发挥到极致,同时围绕这个基点进行创业,作为一个文化创业者的身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对于人文摄影领域而言,你的模式非常成功,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耳:好的谢谢。摄影是我的饭票,也是我的理想,更是我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