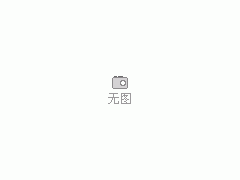和沈阳相距在五百公里左右.
东方红林业局地处黑龙江东部,乌苏里江畔的完达山林区,施业区面积 东方红林业局58万公顷。行政区域分属鸡西、双鸭山市所属的虎林、饶河、宝清三县市。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宝饶公路、南始阿布沁河、北至威山大岭。东西宽68.5公里,南北长93.5公里。局址设在虎林市东方红镇。现属于黑龙江省森林工业集团总公司牡丹江分公司。

地理坐标为132°27′----134°05′,北纬46°10′---47°01′。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宝饶公路、南始阿布沁河、北至威山大岭。东西宽68.5公里,南北长93.5公里。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强调中国今后"当图仿制轮船",以此"为海疆长久之计"。两年后,左宗棠又把仿造轮船的主张同"求强"思想结合到一起。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他对"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而感到"愁愤何可言",主张"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这表明左宗棠谈论洋务的思想已开始萌芽。他把当时与外国打交道的事务称作"洋事",而不用习称的"夷务",表明他的意识比那些习惯于闭关而视西人为"夷"的人们多少有点开明之处。而且他还指出:"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可见他已朦胧意识到中国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
首先,对"夷"、"洋"的看法。"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化而来。明清之际,来华的外国人被称为"夷人",成为惯语。鸦片战争前,伴随着外国武力进逼的步步加紧,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苏松太道吴其泰在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的字样,认为是对他的"凌辱",在抗议中说"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双方引经据典,进行舌战,吴其泰只好改称"该商"含混过去。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而在谈判现场的吉林副都统咸龄却搪塞说,孟子曾把舜称为"东夷之人也",可见"夷"字不是蔑称。似乎战败的面子要恃口角占上风来挽回,可谓昏愦。尽管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还是在不书写"夷"字的情况下签订了。左宗棠能较早地把同外国打交道的事情称作"洋事",说明他并不是在文字的用法上囿于成见,关键是如何寻求御外之方。
其次,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认识。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在上奏描述泊于虎门之外英国兵船的情形时说:"该夷人除炮火外,一无长技"。"倘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则反噬,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而实际上卢坤所依靠的不过是刀矛弓箭、帆篷舟楫,他只是看到了英人的船坚炮利,却根本提不出克敌致胜的方略。与此相反,林则徐在广东主张的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祈裨益实非浅鲜矣"。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谈"议战"时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抡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左宗棠当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虽不如林、魏那样深刻,但他能闪现出设厂造船,"以之制敌"的思想火花,这是难得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朝野上下对"师夷长技"普遍取敌视态度,林则徐"制炮造船的建议被道光皇帝朱批为"一片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也遭到守旧势力的诋毁,林、魏的主张只能束之高阁。第三点是"变局"观的出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黄钧宰首倡此说。他指出,中国人"初不知洋人何伏,英法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②此后,黄恩彤也说:"迨英吉利立市开关,粗角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均数百年中外一大变局也。"变局观的提出,对于重新审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此时的变局思想还主要基于对面方列强不断东犯的初步认识。左宗棠对英国"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所发出的惊呼,恰折射出他对变局的最初理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探讨"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在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捉刀"而作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提出了如此见解: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此次款议虽成,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史学界常以此说把曾国藩视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而真正的倡导者当属左宗棠。事实是,左宗棠能够提出这一主张并非偶然,这恰是他自鸦片战争时期就建议"讥造船之厂","更造炮船、火船之式"想法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以曾国藩的名义上奏的形式,率先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将来学习西方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这就为几年后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举动之开始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具有倡导性的历史作用。因此,可以把此说定为左宗棠洋务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强调中国今后"当图仿制轮船",以此"为海疆长久之计"。两年后,左宗棠又把仿造轮船的主张同"求强"思想结合到一起。他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绸缪也。
这表明左宗棠以谋求自强为目的的洋务思想业已成熟。所以,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关于筹议洋务事宜的奏折中认为:"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悖,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必须"习造轮船,兼习驾驶"。对此,左宗棠说他"怀之三年,乃有此请"。这一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函中也说:"宗棠于此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可见,左宗棠在同治二三年间已决心仿造轮船,至同治四年他把仿造轮船纳入"自强之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对外国的"火轮兵船之制",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即已予以注意。他在任闽浙总督后又与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往返讲论,渐得要领",且"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因此他才敢于力排雇船和买船的议论,毅然提出自造轮船的设想和具体计划,并反复向清廷和总理衙门陈述防止外人干预和不为浮言所惑的主张。左宗棠说:
"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至自造轮机成船,较买见成轮船多费至数倍,即较之购买见成轮机配造成船,亦费增过半,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饥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与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见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肯代为打算乎!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着,人皆知之。其所以不敢遽议及此者,以事体重大,工费繁巨,难要其成,遂莫执其咎。其留意此事者,又率存姑为尝试之心,欲泯其学习制造之迹,彼亦靳不肯与,固无如何。兹既开设船局,名正言顺,彼无所庸其阻挠,我亦无所庸其秘密。……现在洋人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者。实乃暗行阻挠之意。合计自始事至威事五年之中,需费至三百万两,可谓多矣,然而果有成,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乎在此!惟赖朝廷坚持定见,力排浮议,方能宏此远谟,持此险局。……宗棠首倡此议,所恃者由寒素出身,除当年舌耕所得薄置田产二百余亩外,入官后别无长益,人所共知。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惟赖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所惑,则事可有成,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自强之道,此其一端。"设厂造船遇到重重阻力,而左宗棠敢于承担风险,并且抱有很大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曾国藩、李鸿章所不及的。
左宗棠把制造枪炮、轮船都视为"自强之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谁的决心更大,考虑得更为深远。显然左宗棠把"制造轮船"看作"实中国自强要著",强调此举"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做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并且希冀由此"去海之害,收海之利",为"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左宗棠以仿造轮船为主的"制洋器"思想能达到如此高度的认识水平,这正是李鸿章等人所望尘莫及的。
左宗棠"求强"思想的另一主要内涵是"采西学"。他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上奏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他致书总理衙门也说:"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固非习其图书、算学不可,故请于船局中附设艺局,招十余岁聪俊子弟,延洋师教之,先以语言、文字,继之图书、算学,学成而后督造有人,管驾有人。"同治五年(1866年)底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恰开近代军事工业兴办新式学堂风气之先,并与前此设立的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遥相对应,代表了近代以创办新式学堂来引进西方"长技"的进步趋向。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江南制造总局于同治八年(1869年)将广方言馆并入,作为局内所设学堂。天津机器局于同治九年(1880年)设水师学堂。"采西学"的结果使得"制洋器"的水平不断提高。诚如总理衙门大臣奕?所说:"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上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亦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固非臣等数人之私见矣。"奕?所谓京营拣派兵弁往江南制造总局学习一事,是指北京神机营在训练威远队时需洋枪洋炮,派人到上海学此技术。这同福州船政学堂聘外国教师传习西方科技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但奕?把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与"采西学"相提并论,且视此为"自强之道",这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左宗棠积极倡导"采西学",并身体力行地率先忖诸于实践,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左宗棠"求强"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确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积极作用,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实开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之先河。尤为可贵的是,左宗棠在晚年能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他的"求强"思想。光绪十一年(1885年),担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上奏总结了以往的造船情况,他说:
同治五年奏设船政,于福建仿造外国兵船,甫蒙俞允。即拜西征之命,一切制造,经历任船政大臣斟酌办理,不敢耗费财力。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胁快船,较旧式稍利,然仿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船中枪炮概系购配外洋,兵船所用又有多寡利钝之分,所以夷衅一开,皆谓水战不足恃也。
左宗棠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者,并不因仿造轮船的式样陈旧而掩掩遮遮,他主张迎头追赶西方的先进造船制炮技术,建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他指出:
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如能筹得二三百万金,矿、炮并举,不惟炮可自制,推之铁甲兵船与夫火车铁路,一切大政皆可次第举办,较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得失显然。……此次法夷犯顺,游弋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及时开厂制办,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穆源铁矿,臣接见闽省官绅,均谓便于开采,似应委员试办,并拓马江船厂兴工铸炮。臣又闻江南徐州铁矿,矿苗之旺甲五大洲,若能筹款开办,即于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
这不仅表明左宗棠举办洋务的认识比60年代深入了一步,同时也反映了军事工业对民用企业的创办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左宗棠还说: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敕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伏乞寝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左宗棠的这份上奏,实揭开了晚清第二次"海防之议"的帷幕。清廷在"上谕"中称:"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驰,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画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可见清廷不仅采纳了左宗棠"请旨敕议"的建议,还提出了"大治水师"的海防新目标。左宗棠的"求强"思想正是在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得以升华。